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学者严海蓉和四名青年学者在《开放时代》发表引入注目的专题文章,试图在三农问题上发出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眼中,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
他们不仅批判主流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也与黄宗智和贺雪峰对话。这两位著名的三农专家认为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小农经济不仅具有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贺雪峰称这样的观点为小农经济派。
与此不同的是,严海蓉、陈义媛、孙新华、陈航英、黄瑜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已经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小农虽然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在丧失主体性,而开始直接地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化农业。他们正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农业资本化的危险。
“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
在严海蓉看来,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关注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弱势地位;而在在新三农问题里,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和分裂。
农业现代化是否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长期以来的主流模式都是规模化和资本化,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而中国人多地少,并不适合这样的模式。对市场的崇拜使得资本化农业、化工农业变成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澎湃新闻记者就一系列问题采访了上述五位学者。
澎湃新闻:2006中央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在你看来今天三农问题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是什么?
孙新华:应该说,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国家也将大量惠农资金投放到农村,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代。应该说农民种田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工商资本大举进军农村;各级政府也在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口号下,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和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农民的土地,而且还将国家的各种惠农项目重点倾斜投入到城市工商资本经营的土地上。因此本该由广大农民分享的利益被城市工商资本攫取。
这样一来,尽管农业在一些指标上有所改观,比如在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和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都有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不见得提高甚至很多都在降低),但是这又和农民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农民不仅无法再分享农业利益和国家的资源投入,而且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使原本具有一定活力的村庄也在不断走向衰败。
所以,我觉得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这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是十分不利的。
严海蓉:虽然中央废除农业税的政策有助于农民减负,然而原来的三农问题已经演变成新的三农问题。在我看来,新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和农村生态危机。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主要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主体地位弱势的问题。在新三农问题里,我们看到的是主体性的分裂和变异。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这是基本的事实。
在新华的回答中,仍然是把“农民”当作一个未分化的整体,而这正是我们从经验到概念上应该破除的一个误区。“与广大农民争利”的不仅是下乡的城市工商资本,也有农村内生的种植大户。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拿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2012年最高的20%农户的收入是最低的20%农户收入的8.2倍。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在2001-2011年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10%的农村居民收入比最低的10%收入增速快两倍。
有些人认为农村的分化主要是由于在外务工或经营带来的,在农业经营方面则分化不显着。其实不然,新世纪十年间(2001-2011)农业经营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前十年(1991-2000)年期间要大,即农业经营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实际上自农村改革以来,中央的政策就在推动农民分化,鼓励农村大户、专业户的出现,帮助成就了今天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伴随着农民分化,农业已经开始资本化。我们认为在农业资本化中,大户、专业户的积累产生于农民分化,可以视为自下而上的资本动力,相比较而言,资本下乡则是自上而下的资本动力,也有新型经营主体—如很多合作社,结合了这两种动力。如何看待农业资本化?主流欢迎和鼓励资本化。“小农经济派”的学者反对资本下乡,反对政府帮助资本下乡,但是鼓励或默认农村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黄宗智教授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没有造成无产化,即农业雇佣劳动的比例很低,只有3-5%左右。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雇用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大约在20-30%左右。土地的逐渐集中、雇佣劳动的显着增加——这也是农民分化的一个体现,使得中国有走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趋势。
中国农村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环境生态危机。严重依赖化肥、农药、农膜的化工农业已经是造成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因素。举个例子,在单位面积上,中国化肥的使用量是国际公认安全上限的1.93倍。环境生态危机威胁着城乡的公共健康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黄瑜:如严海蓉提到,我国的“化工农业”已经造成严重的污染,可是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重视。工厂污染了环境可能不一定会影响生产,可是农业离开了健康的生态环境是无以维系的。另外,国家目前对农业方面的扶持,除了补贴之外,很多时候是以项目的形式发放的。表面上看,项目的招标是公开公平的,可是,一份项目申请书最少都要上百页,普通的农民很难弄的出来。因此,项目多由龙头企业独占,而普通农户难以获得。
澎湃新闻:农业现代化是否离不开规模化和资本化?
陈航英:中国农业的出路势必要现代化,所以问题不在于农业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于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当前选择的道路是以资本为主导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所谓的“新大陆模式”或者“旧的农业范式”。这一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先就是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情况,另外更为严重的就是它会让我们重新走上让广大农民无产和半无产化的老路,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其带来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自然层面都是我们所承担不起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当前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之外,寻找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呢?
陈义媛:今天农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的确已经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与中国户均不足十亩地的农业经营状况出现了矛盾,我们的确有规模化的需要。我同意航英的观点,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农业现代化”,而是要讨论什么样的 “农业现代化”。今天的政策话语中,“农业现代化”基本就等同于“资本化”和“规模化”,或者说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规模化,无论是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还是所谓的家庭农场。
这几类主体尽管具体经营方式有不同,但基本逻辑有一致性:使用相当比例的雇佣劳动、以利润最大化并扩大再生产为目标。他们与普通农户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质的不同。这几类主体中,有龙头企业这种外来资本下乡的形式,同时也有家庭农场这类从农村分化中内生的资本形态,分别对应着严海蓉老师和我的文章中指出的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和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驱动力。
国家对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补贴和扶持,且扶持力度近年来有增无减;然而,即便没有政府的补贴,一些企业、种植大户也在不断的试错和失败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营策略,并且能够盈利。也就是说,这类经营主体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国家政策扶持而偶然出现的,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并且这股日渐强大的力量正在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
遗憾的是,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构成了我们今天对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想象。人民公社时代的农业经营模式尽管遭到很多批评,但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下讨论,暂不赘言。集体时代的农业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类想象?将村集体土地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化,发挥机械化优势,在集体中按劳分配,并逐步积累;在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创办集体自己的农产品储藏、加工企业,使一小部分劳动力在农业经营领域,而将其余的劳动力组织在集体的工业企业中,使农业增值收益留在村集体,每个集体成员平均分享。将劳动者——而不是利润——作为规模化的主体,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
孙新华:我也觉得农业现代化肯定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但关键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正像义媛所说,长期以来主流所认同和实践中的主流模式都是将大规模的农场即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等同于现代农业。这其实只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在新大陆国家人少地多,比较适宜这种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而粗”,单位产出率并不高,尽管劳动生产效率比较高。
而中国恰是人多地少的国度,我们的广大农民需要种地,我国的粮食安全又要求保障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这些都限制了我国走大而粗的新大陆模式,而更适合走传统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即在以小生产者作为主要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实现农业现代化。
所以,假如现代化一定离不开规模化的话,规模化不一定非得是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还可以是通过“小生产+大合作”实现规模化。
澎湃新闻:小农是怎样变成无产、半无产者的?对这个群体意味着什么?
孙新华:正是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大行其道才导致了小农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必然要集中连片地进行大面积的土地流转,而流出土地的农民又是分化的,有的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他们愿意将土地流转给资本,获取更高的租金;还有更多的农户是不愿流转的,一部分农户希望自己耕种,一部分农户自己还想流入一部分土地,还有一部分虽然暂时不种,但过几年可能还要种。这就与资本流转土地的需求构成了矛盾。
而现实中,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不仅是资本的需求,也是地方政府出政绩、造亮点的好途径,因此地方政府会帮助资本进行大面积地集中连片的流转土地,其主要做法是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当然,现实中也有少部分资本借助村干部和地方灰黑势力直接强迫农户将手中土地流转出来。即农民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必然是违背农民意愿的。
对于这些农民,后果必然是悲惨的,只有少部分农民被强迫离开土地后生活状况有所好转,大部分都是大不如前。他们或者疲于奔命地劳动但经济收入还是大不如前;或者无事可做,身心无处安放,时间无法打发。
黄瑜:近十年来,我们所看到农村的一个明显变化是资本下乡的情况日益普遍。这个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明显。由于出口放缓,再加上和制造业本身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导致许多的城市工商资本开始投往农村。
当然,许多这类资本大多靠国家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等隐性方式的支持,才取得投资农业的启动资金的。国家希望这些资本能够推动农业的“现代化”,用机械化生产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可是,这种工业化生产所遇到的环境危机在此自不待说,更严重的问题是机器排挤劳动力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为了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奉献了他们的一生,到头来却落得被机器取代的结局。在“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年代,广大“无产化”的劳动者将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学者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陈义媛:今天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凸显。就土地流转来说,政策宣传中常常指出的是,这些将土地流转给公司、大户的农户,将获取三份收入:一份是土地流转费、一份是给企业或大户作农业雇工的收入——在土地流转协议中,常常有一条说明,企业或大户在雇工时,需优先考虑流转了土地的农户、一份是国家的农业补贴。还有宣传说,将土地流转给企业或大户以后,农户可以放心地出去打工,可以获取更多的打工收入。
实际上,且不说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尽可能地减少劳动力成本,用机械替代劳力;而且这些企业或大户通常不会雇佣本地农户,因为本地农户太容易联合起来与企业/大户形成对抗,不利于劳动监管。即便外出打工,今天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能否容纳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这些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进城以后打不了工,回乡以后又没了地,又该如何?这是在土地流转的主流话语中被屏蔽的问题。
也许有人说政策现在提的是“适度规模经营”,不会排挤过多劳动力,但如前面所说,在外部竞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适度规模”会是一个稳定状态吗?那些处于“适度规模”下的经营者不会分化吗?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或“升级”吗?
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就我目前的调查来看,答案不容乐观。我认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被流转的这部分农户成为了无产者、半无产者。即便没有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也一样面临无产化、半无产化的问题。
陈航英:要回答农民无产化、半无产化的问题,一个首要的前提是对中国“农民”群体先进行一个讨论,这点海蓉老师也提到了。当前学界,无论是主流的经济学者,还是亲小农学者,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忽略了中国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在他们的论述中,中国的农民依旧是一个相对于城市居民的同质性群体,依旧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小农。但实际上经过 “去农民化”的洗礼后,农民群体内部分化已经是非常显着的了。我们不能再把农民看成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动辄就谈9亿农民。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谈到底是“农民”群体中哪部分人正在变成无产、半无产者。在我看来,正在成为无产、半无产者的农民主要就是那些“半工半农”的普通农户家庭。对于导致这些普通农户家庭不断无产、半无产化的原因,我认为海蓉老师和新华老师的论述已经很清楚,主要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所导致的。我的调研发现,农资经销商、农业大户和农产品加工销售商这三个主体相互结合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占据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主导地位,掌控了农业生产中的大部分资源,他们是资本化农业的主导者。而普通农户手中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正不断地流向前一个群体,因此在生产、服务和销售方面处于从属的半无产化地位。
无产化、半无产化对于普通农户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不赞同新华老师的看法。无产、半无产化并不一定代表着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是说这个群体在其所处的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被压榨的地位,在城乡流动中不得不接受“妻离子散”的家庭生活。
澎湃新闻:对于目前主流的三农学界,你最希望反驳的观点什么?
孙新华:农业现代化就是规模化和资本化。
严海蓉:我认为需要迫切反思的观点和政策是对市场的崇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涉及到对粮食的定位问题。我们知道国家安全、民生安全、生态安全是公共品,而粮食与这些公共品有密切联系,因此国家也把粮食安全的当作国策,既然这样,粮食应该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而不应该完全是商品。
还需要反思的是对资本化农业的憧憬,认为资本化农业、化工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别无选择。其实,这种旧的农业范式已经遭遇可持续性的挑战,国际上,农业范式创新已经开始,联合国把2014年定为“家庭农业年。”我们不应该守旧,而应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和资本化农业之外,探索新的道路。
陈航英:反驳崇拜市场的观点,特别是那些认为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和水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把粮食这样的公共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把一个国家、民族的粮食安全任由市场来支配。我国东北大豆产业惨败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依靠市场的不靠谱。我们需要记住习总书记的话,“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要牢牢端住,也不能依靠当前正在践行的美国式的资本化农业道路。在这一条道路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产生,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广大农民则不断无产、半无产化。即便是有任何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最终也只能沦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一个工具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这条道路还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危机。为了增加产量,掠夺性抽取地下水、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已有使农业生态达到崩溃边缘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一条于广大群众有益的、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现代化道路。
澎湃新闻:想要扭转这一进程的话,你认为最迫切需要改变的一点是什么?
孙新华: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对新大陆模式的盲目崇拜,对中国小农的过分贬低。
严海蓉:我认为需要的是破除对市场、对资本化农业的迷信。
陈航英:加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统”的一面。无论是“三权分置”,还是土地确权,现行政策都在不断完善个体“分”的一面。而作为“统”的主体的村集体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正不断被个体的承包经营权所架空。“统分不结合”的现状已经使得具体基础性、公共性的水利和其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停滞不前。即便是国家投巨资在各地进行农地改造项目,但在项目完成后也因为缺乏管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这些方面必须加强村集体的“统一经营”。加强村集体“统”的一面,也有利于真正做到把广大普通农户联合起来,加强其生产者主权,使其在市场之中不至于“孤军奋战”,受到各类“中间商”的盘剥,我们也会更少听到“菜贱伤农”、“果贱伤农”、“奶贱伤农”等新闻。而且集体的“统一经营”也更有条件摒弃不可持续的化工农业,转向可持续的生态农业,这在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同时,也确保了食品安全,保障了消费者的食物主权。而于国家而言,也有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维护国家食物主权。
本站推荐: 买得易 折扣信息 网上购物大全 买得易网 双鱼座 水瓶座 摩羯座 射手座 天蝎座 天秤座 瑰夏咖啡 咖啡网 咖啡 手磨咖啡 咖啡豆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云南咖啡 花魁咖啡 耶加雪菲 精品咖啡豆 瑰夏咖啡 咖啡网 咖啡 手磨咖啡 咖啡豆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云南咖啡 花魁咖啡 耶加雪菲 精品咖啡豆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01-10 13:4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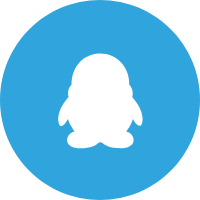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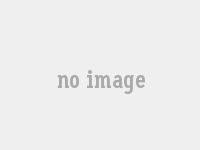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