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完成向现代化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就是在农业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改换职业和居住地的迁移过程,因此可说土地在其中扮演了枢纽作用。这是我这些年来集中研究土地问题的原因。周其仁教授是我尊重的学界同仁,他的几次主动不吝赐教,包括最新这篇“城市化为什么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见《经济观察报》2014年9月8日)促进了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我也知道,周教授的土地观点绝非少数派,而是代表了一大批向政府建言的经济学家的学界主流意见。尽管如此,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我再作此文,以求教于其仁兄并方家大众。
人的城市化是别扭,还是切中要害?
周教授上次说认识我多年,不知我研究土地问题,而且不研究就一下发表宏论,颇有责备之意。故我仔细解释其实我十几年前就从农民进城打工开始研究人的城市化问题,也是下了很多年功夫,并非“不研究就未必不能提出正确意见”的轻率之举。不料解释后周教授这次又有怪我研究得太早了之意,他说“至于当年怎么提出,以及是不是还有别人更早提出,我没有查证。从现在情况看,不论原创属谁,‘人的城市化’——这个‘术语’——我就觉得有点别扭。”
持续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化要了农民的土地,却无法接纳农民。
其实提出问题只是为了研究解决,谁先提后提都没有多大关系。但人的真正城市化,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件大事。特别是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进城不能落户和市民化的严重问题。故我当年分析说“城市户口垄断对中国发展的巨大阻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相对资源的人口压力,中国要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的高速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这两大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太低。”“截止到20世纪末,按照统计的城市非农业人口,仍在20%左右徘徊,其他10%被列入城市人口的仅是指目前进入城市和小城镇的农村人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合法的城市户口的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正好完全倒置,是我国经济结构最大的不合理,是国家内需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最显着标志和贫富差距拉大占比中最大的因素”(见《破除垄断坚冰》、《时代财富》杂志2001年第1期)。这个矛盾由于我国随后即加入世贸而得到缓解,因而并没有引起重视。故2006年2月4日,我又固执鲁莽地给时任国家主席和总理郑重去信,直率批评当时的国家政策重心,指出“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世界上属于最大之列。这个矛盾是中国今后20年的主要矛盾。但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三农,而在城市化”。“中国社会当前迫切需要提出和实施的是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个战略的出发点,首先是在城乡统筹的框架内解决已经进城农民的身份和地位的平稳转变问题,其次是规划和布局每年1500万左右新增农民进城落户问题”。但只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被全球化一时掩盖的人的城市化问题才重新更尖锐地浮上水面,并成为近年来政策和社会的热点。
尽管如此,我从没说过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创见,相信也许有人更早更多地从不同角度关注过这一问题,但周教授在文中说“以我所知,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文贯中教授,”则是肯定不严谨的。周教授在为文贯中教授今年新书《吾民无土》所作序中专门指出“那是2009年7月”。其实那时国内关于人的城市化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故文教授自己在书中也是说,由于城市人口包含了2亿农民工,“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当扣除农民工的份额,因而只有36%左右,并将官方数字戏称为‘伪城市化率’”。而据我看到,文教授在2007年就对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有所怀疑,不过作为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直到2008年他回上海兼职任教,他发表的文章还都是采用官方数据。至于周教授说文教授提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涉及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与城市人口以什么比例关系增长更优,是技术经济层次的另一个问题,需要专门的比较和研究。文教授在书中也没说自己提出而是援引他人关于中国城市化“化地不化人”的观点,表示他很赞成这个“一针见血的归纳”。顺便说一句,文教授是笃信唯有土地私有化能够救中国的学者。他回国最初几年与我有过多次交流。近年来我们在土地和城市化问题上的观点越离越远。不过,尽管观点不同,他仍然是我尊重的学者。
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谁闹了笑话?
周教授援引一句我在他处写的“我国法律现在讲的集体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集体拥有的土地”,然后大发议论说,“不敢相信,作者对农村集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历史及演变居然如此毫无常识,全不知道我国绝大部分集体土地属于过去的生产队——也就是今天的自然村、村民小组或“合作社”——而并不属于‘行政村’(即过去的‘大队’)”。周教授教训说“无须太劳神,只在百度百科查一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就可知现村民小组(生产队)拥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占总面积的90%以上,而不至于闹笑话。“自带一个笑话水准的硬伤上场,岂不自曝其短、授人以柄?华生还自我介绍‘15岁就下乡插队当了多年农民,后来也不时做一些农村调查’。如此这般,怎么连‘集体土地’主要是个啥也搞不准?容我写出心中之忧:对远比中国集体土地复杂、体验又远为不足的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等地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开发等诸种复杂事务,那些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满世界跑舌头讲下来的‘事实的陈述’,怎能让人读来觉得踏实?”显然,周教授自称“不好意思加注一笔”,不是多余,而是以小见大,抓住对方的一个“硬伤”,进而怀疑和否定其全部陈述与观点的可信度。
周教授这样嬉笑怒骂,抓住一点就将对手一棍子打死,自然惬意。但也包含了一个小小的风险,就是这个他不容置疑的“硬伤”和“笑话”,万一被证明是他本人的错误或疏漏,他全部嘲讽和否定的对象,就完全落向了自己。因为周教授所说的集体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只是1962年颁布的《人民公社60条》中的规定,其中第二十一条明确“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 1975年宪法修订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写入了“七五宪法”第七条。但是对法外世界情有独钟的周教授似乎不清楚这个提法在“文革”结束后修订的1982年宪法中就已被删除。“八二宪法” 第十条只是笼统地说“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之外,属于集体所有”,不再涉猎归哪一级。周教授好像更不清楚的是,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明确取消了集体土地归生产队即现村民小组所有的说法,其第七十三条首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此后的《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自此全部都照抄这一条款。照顾到历史情况,一些法律补充指出,已经属于乡镇或村内两个以上集体组织所有的,可以继续属于。可见,我前述文章所述概念相当准确,并没有任何错误。实际上也正是基于这一法律所有关系,我国从广东到北京南北等各地发生的土地冲突和营私舞弊,都是集中出在村委会村干部这一级,而不是在村民小组和村民小组长那里。周教授单凭一个网上搜索的别人加工的信息,既不看法律,也不看实际,就敢自负地嘲笑别人援引的正式法律规定是“硬伤”和“笑话”,真不知叫人说什么好。
尽管周教授摆了这么大个乌龙,我并不想照搬他的逻辑,断言他的各种观点及对海外情况的“略作辨析”也就因此全部存疑作废,相信周教授今后也会对自己这种网上快速搜索的信息存一份戒心,进行核查,对别人的研究也增加一点尊重。我还想说的是,周教授一时疏忽犯错也并非不得了的大事,但那么多媒体和学者借周教授的话大做“硬伤”和“笑话”的文章,却无人稍微做一点原始资料的查验工作,这确实说明今天的学术和媒体环境的浮躁,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以上我们跟着周教授的思路厘清的其实只是两个小问题,当然它提醒我们学问无论做到什么程度,治学态度仍需严谨;再觉真理在握说话也要留有余地;别人观点对错更无关人品。只是鉴于小问题都这么绕人,下面的大问题我们再沿着周教授设定的思路,肯定更会被绕得头晕眼花、不知所往。因此,下面我将聚焦争论的几个实质问题,这样大家即使达不成共识,至少也能明白分歧所在。
分歧之一:
农地农宅入市,还是建筑权归属
周教授高举着农地农房入市的大旗,从道德高地上杀将下来,但他的这一刀本来并不应砍向我。因为我再答周其仁教授的文章中已经明确表示“农地农房入市倒确实与小产权房违建性质完全不同,是符合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方向上说我并无异议”。我还在三答中专文讨论目前情况下农地农房入市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如何解决的方法途径。那么,周教授为什么一定要在农地农宅入市的旗帜下对我这个同道者大加挞伐呢?
原来周教授关心的并非农地本身的流转入市。如我之前所说过,农地限于农业用途的流转入市现在全国搞得风起云涌,流转量早已超过四分之一。不过周教授对此并无兴趣。按现行规定一户一宅的农民自住房和宅基地的流转或转让回收,虽然比较复杂,文件政策上也有松动,正在准备试点。周教授对此也兴趣有限。周教授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去掉《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农地不得转让用于非农建设这一条,或如他所说将“不得”改为“可以”,从而为农地转让用于非农建设敞开大门。而我介绍和主张的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的分离、土地用途与规划管治和建筑不自由等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周教授自然气不打一处来。故周教授恨恨地说,“我认为其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个‘建筑不自由论’”。
从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城市化过程中确实会有大量农地转为城市建设之用。不过这主要是发生在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周边。而非城郊的农地还是会用于农业,更大量的农村村落还会复垦为农地。远郊农村的部分农地也会在城市化过程中用于非农建设,但这主要是随农村现代化发展所必须增加的道路等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用地。因此,对广大非城郊农村来说,农地农宅入市,无论是因规划管治,还是因市场规律,增值和变化都会很有限。看看别人走过的路和现状就知道,非要说农地农宅入市就会给远郊农民带来多大的利益,那肯定是假话。真正大有意义的,是城镇尤其大中城市周边的农地和村庄。故周教授嘴上喊的是农地农宅,眼睛盯的是城郊土地开发。他这些年组织的调研连续不断,始终没有离开重庆、成都、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城郊,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
由此可见,有人欢呼农地农宅入市是九亿农民的福音,显然是混淆视听。农地以何种方式入市只对几千万城中村城郊村原住民及土地投资投机者利害巨大。因为快速城市化转型使一国土地价值发生重大结构性改变。在真正的农地农宅价值变化有限的同时,转为城市建设的农地会获得或百上千倍的增值。人口的不断城市化集聚和社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在极少量城市建设土地上的堆积,使得城市中的商业化土地成为造富机器和财富分配的最普遍形式。
因此,真正的分歧在于,周教授打着农地农宅入市的旗号,要放手推动城中村城郊村的土地转让开发入市,我则认为这涉及全体国民的重大财富分配,绝不可让少数人分肥与自行其是。因此,尽管我支持从改革方向上说农地农宅可以也应当入市,但要循序慎重从事,严格区分城郊非城郊,区分在农地大旗下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即使对可以商住开发的土地,现代社会也不能没有规划和容积率管治,因而自己的土地上自己也没有空间建筑权。而且这不仅农民没有,城市居民也没有;中国公有土地上没有,西方私有土地上也没有。这就惹来了周教授《辩“建筑不自由”》的几篇批评文章,对我所说的西方建筑不自由深表怀疑。待我详细介绍了发达国家以及东亚的用途与建筑管治的情况后,周教授这次又教训道“具体到城市化课题,多看看别家在城市化率达到70%以前的举措,不是更有针对性吗?自己的城市化率不过略过50%,非要把达到高度城市化国家——城市化率达到80%-90%——很晚才采用的办法搬来,人家毫发无损,自己憋个半死,很过瘾吗?”
看来周教授对我所介绍的发达国家现状已经多少查证,不再斥之为“荒诞不经”和“怪论”了,但又训斥我引述情况的时间和历史阶段不对。其实我原本既介绍欧美历史上的土地建筑司法实际,又着重介绍东亚的日韩和中国台湾,就是因为我们正处在几十年前人家的发展阶段上。不过当时周教授并不爱听。他一定是忘记了自己半年前在《辩“建筑不自由”》一文中所说的话。因为他在那里说,据他所知,美国的分区和规划管治自上个世纪以来是越来越宽松了,“在这种情况下,只对上世纪20年代以前的美国判例引经据典,怕有误导读者之嫌”。可见,只要不符合周教授头脑中固定的建筑自由的市场信条,对别人的案例和实际,时间引晚了不行,引早了也还是不行。
本站推荐: 买得易 折扣信息 网上购物大全 买得易网 双鱼座 水瓶座 摩羯座 射手座 天蝎座 天秤座 瑰夏咖啡 咖啡豆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咖啡网 云南咖啡 手磨咖啡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咖啡 耶加雪菲 瑰夏咖啡 咖啡豆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咖啡网 云南咖啡 手磨咖啡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咖啡 耶加雪菲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03-20 23:5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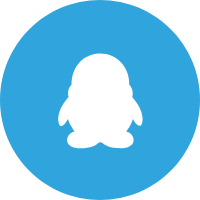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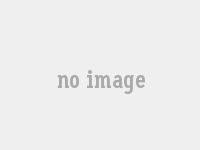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