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力于收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农村口述历史
口述史研究的缘起: "没有民间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徐书鸣:郭老师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坚持进行田野调查的工作,能否简单介绍下您口述史研究的项目背景?
郭于华:这个项目开始于90年代中后期,当时,孙立平老师在北大,我和沈原老师在社科院,应星那会儿还在读书,另外还有一小帮硕士生、博士生, 我们想做一个定位在中国社会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口述历史研究,于是孙老师和我就主持了这样一个项目。当初的设想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找六个村庄,分别收集农民的访谈资料,数年来也一直在致力于这个计划的落实,但实际只开辟了四个村庄,即河北西村、陕北骥村、四川柳平村(现在属于重庆)和东北石湾村。
袁训会:为什么选这几个村庄?只是一个单纯的样本吗?
郭于华:当时是希望能在不同区域选择样本,既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我们最后两个村子是想选在南方,但是力量不足,因为选南方的村子--广东或者是江浙一带--有很多困难,比如方言的问题。而且参与的同学在毕业以后,很多都不在这一领域研究了,人手不够,所以剩下的两个村子没能开辟出来。另外,尽管四个村子的调查都是基于口述史的思路,可是完成的程度却不一样,骥村的调查比较全面,基本覆盖了其二十世纪下半期的历史。其它几个村子的调查方向各有侧重,有的村子"土改"做得比较全面,有的则是"合作化"做得比较多。 这个口述史的项目的初衷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若要关注今天的转型,首先需要了解转型前中国社会的状态。很多人都认为转型遭遇到瓶颈,已经转不下去了,甚至有人说改革已死。这就使得转型前--49年到改革开放之间--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更加必要,既包括其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也要关注到它在现实中的运作模式。所以研究当下中国的任何现象,转型问题都避不开,而对转型过程的分析,又需要一个历史的脉络。以前社会学对历史不太关注,当我们现在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回顾过去的历史时,发现当下的历史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只包括官方的历史,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讲述,其中有很多的掩盖、扭曲,甚至编造,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呈现历史。历史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历史一定有问题,一定要被质疑。以往的历史中,无论是官方历史还是学者研究,那些最普通的村民、村妇,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经历和体验是被忽略的。所以当时的我们有一个抱负:希望能够知道这些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说它是回顾也好,追溯也行,我们的目的是要搜集、记录这样一段历史,毕竟没有民间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历史不能只以唯一的方式存在。
其二,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判断,并能在理论上或者学术上探讨,所以我们提出"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对它的界定,需要看其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是什么,需要通过具体的史料和亲历者的讲述,来理解其机制、逻辑,特别要通过一个过程性的研究把它的机制和结构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学术理论上的追求。
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的推进会非常困难,因为搜集历史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理论的总结也不是特别有底,搜集、记录了之后,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论抱负尚是未知,只能从倾听、记录、呈现再到研究分析,逐步推进。
这就是我们口述史研究项目的大致背景。
从"领导"到"亲戚":与村民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
徐书鸣:田野调查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才能融入到农民的生活情境中。您在调查期间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吗?又是怎么解决的?
郭于华:在这方面,我们有跨学科的优势,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就要求研究者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从而能够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
当然还要求相当长时间的投入和互动,不可能一两次接触就能跟农民熟络起来,让他们相信你,什么事都愿意跟你讲。
徐书鸣:能举个例子吗?
郭于华:比如我们在骥村,第一次去调查的时候,当地人用水还需要挑,因为他们的窑洞都在半山上,要下到山沟里,从那儿的井里挑水,再爬回山上。当时,我们的调查团队有好几个人,房东家的用水量一下增加了很多,他们要挑更多的水才够用。给房东增加负担,我们觉得挺不好的,于是自己去挑水。我只能挑那段平路,因为挑上山,中间不能放,我根本挑不上去,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男生,只能是我挑到山底下,他挑上去,的确是一件挺费劲的事。
第二年去调查的时候,他们村子开始有人试着自己家打井,然后埋个深水泵,把水泵到山上去,这样就有自来水了。我们团队的几个人商量后,由我们出钱,房东家出工,在他家山下装土豆的窖里打了口井,当时还请了阴阳先生,因为不知道哪儿能打出水,只能由阴阳先生观测后决定。对此,我们都觉得特别逗,不过好像真撞上了大运,一次就打出水来了,水质还挺好的,然后把深水泵埋下去,又铺了水管。怕冬天水管冻坏,铺管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要先在他们家窑洞顶的山上修一个水窖,把水抽到山上,再在山上埋下管道,把水送到房东家。
实际上,与农民交往不需要你刻意做什么,更多是大家用一种友善、真诚,也相互信任和互惠的方式互动。后来跟村子里的人越来越熟,有些村子里的年轻人想在北京找工作,我们也会帮忙。跟他们的关系变得像亲戚一样。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们是外地人,而且是从北京来的,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上面来的,无论怎么解释说我们就是老师和学生,不是领导,也没用。
在慢慢建立信任的过程中,他们的一些民间信仰的活动也会找我们帮忙,比如拜龙王、观音等。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有些顾虑,觉得外面来的人对这些"迷信落后"的东西肯定不支持,有一次,村子里修庙,在重新制作神灵的牌位时,需要有人在牌位上写字,他们村子里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时我跟社科院的罗红光老师在村子里,前党支部书记--他退下来以后就当了庙会的负责人,负责村子里的"社事"--就跑来找我们,特别胆怯地问:"你们都是博士,能不能帮我们写字?"我们俩当时异口同声地说:"可以",答应完之后才觉得有问题,我俩都不会书法!我说:"那咱赶紧练",就去找我们房东家里上四年级的小姑娘,跟她借了毛笔、墨汁,在报纸在上练字,一练发现也不行,哪能那么短时间练得出来?后来想了半天办法,最后从笔记本电脑上调出汉鼎隶书的字体,特别漂亮,写牌位最合适。我们就想了好多办法,把它描到木板上,一晚上没睡觉把五个牌位上的字全给描出来了,还不敢让别人看见,只能在屋里偷偷弄。天亮以后,我们把描上字的牌位放在窗台上,太阳刚升起来,老支书就来了,一看特别高兴,说:"写得太好了!真不愧是博士。"我们也不敢说是描的。
长此以往,他们也知道我们很真诚,愿意跟他们互动互惠、交朋友,交流逐渐就没了障碍,访谈就变成了拉家常。
二、共产主义能否被称为一种文明形态?
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文明"
徐书鸣:您刚才提到了口述史研究的缘起,它是希望提出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新解读,那么"共产主义文明"的分析概念与和现在比较流行的建国史研究相比,其创新之处在哪里?
郭于华:这个概念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刚开始做口述史的时候,我们就多次讨论这个概念,当时我跟孙老师都写过相关文章,认为必须有一个概念能够涵盖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这段历史。有的人把它定义为"共产党文化"或者"党文化"。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范围很狭隘。当然,关于"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会有很多争论,有人说那不是文明,而是野蛮。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厘清:
首先涉及到"文明"的概念。以往对"文明"的理解都是褒义的,强调文明相对于野蛮,认为文明带有启蒙、觉醒的含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就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形式。这不是我们自己定义出来的,埃利亚思的《文明的进程》其实已经这么使用"文明"的概念了。他提到,比如英国人和法国人互相看不起,说对方的行为方式是不文明的,那里的Civilization中的Civil有"礼貌"的含义,有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肯定和骄傲的意思。而我们不妨先不取其褒义的理解。
其次涉及到文明的具体内涵。以往一提文明这个词,我们往往会联想到宏大的物质文明成果(如长城、金字塔)或者是精神文明成果(思想、理论、鸿篇巨制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制度文明,它意味着社会所依赖的组织制度框架,以及在此结构下其具体的运作模式。这当然也是文明的内涵。通常人们容易忽视文明框架下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考、言说和表达,其实这些都与文明有关。
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文明的理解是基于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考察,从基层的视角来理解文明。如果说只做褒义的、宏大的理解,我们就会忽略社会当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共产主义文明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的文化基础、制度安排乃至国民性都不一样。因此用"共产主义文明"这个概念来指代我们所要解析的那段历史,它是成立的,也具有研究的可操作性。我们既然能够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也应该能从普通人的行动与言说中理解文明的逻辑。
本站推荐: 买得易 折扣信息 网上购物大全 买得易网 双鱼座 水瓶座 摩羯座 射手座 天蝎座 天秤座 云南咖啡 耶加雪菲 咖啡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咖啡网 咖啡豆 瑰夏咖啡 手磨咖啡 云南咖啡 耶加雪菲 咖啡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咖啡网 咖啡豆 瑰夏咖啡 手磨咖啡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03-20 23:4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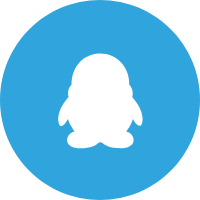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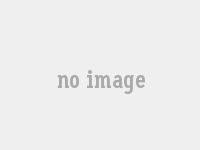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