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人人喊打的福寿螺,在日本竟然被尊称为“稻守贝”!而在原生地阿根廷,不但没人觉得福寿螺有危害,还被生态解说员拿来当作认识地景变迁的代表性物种?
宜兰的友善小农社群天天与螺为伍,从格杀勿论的“打怪”心态,慢慢发现根本不够认识这个最亲密的敌人,于是在今年八月踏上福寿螺寻根之旅,远赴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也到同样有福寿螺问题的日本、菲律宾取经,希望找到从“人螺殊途”到“人螺共生”的可行之道。
.jpg)
执念太深,福寿螺一统宜兰小农江湖
“因为对福寿螺共同的执念,捡螺捡到由恨生爱,爱恨交织。也是福寿螺,把松散的宜兰小农,一统江湖!”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系副教授、土拉客实验农家园成员蔡晏霖笑道。
她是这趟福寿螺回娘家的阿根廷之旅成员之一,还有发起“农田里的科学计划”的动物学博士林芳仪,以及创作者田文社社长林欣琦(绰号Över),三人分别以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艺术家并且也都是农民的角度,重新看待“我们与螺的距离”。
“福寿螺在大家印象中就是坏,秧插下去,一两天就不见了,”甚至像是幽浮过境整片被吸走,“所以我们刚开始也是抱持着除恶务尽的态度。”蔡晏霖解说,惯行农法以杀螺剂对付福寿螺,有机农法则用苦茶粕,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会连带杀死许多水中生物,许多小农宁可徒手捡螺。
于是大家就因为捡螺而发展出革命情感,有人设计捕螺陷阱,有人发明“捕螺神器”(类似煮切仔面的捞网加上伸缩窗帘杆)⋯⋯一耳闻福寿螺在晚上九点到半夜三点最为活跃,小农们就各自套著头灯披星戴月,在田中摸黑捡螺。

找福寿螺拍片,从多物种角度观看田野
可是我们对于福寿螺的了解有多少?许多新农连田螺和福寿螺都难以分辨。作为人类学家的蔡晏霖进一步思考:有没有可能跳脱人类角度,以“多物种民族志”的方式,用水田生物的角度来认识福寿螺与这块土地?
于是破天荒第一遭,福寿螺身上背起了微型摄影机。
“我们找到一只体型特别大的福寿螺,还帮它增肥,”蔡晏霖说因为要符合人道精神,生物负重不能超过体重的十分之一,好不容易黏上摄影机后放回田中,“摄影师”本人却杵在原地,展开“不合作运动”。
此时一只非洲大蜗牛从旁悠然经过,众人立刻把脑筋动到它身上,因为它也会下到田里,跟福寿螺生活环境重叠。幸好蜗牛不负众望,背起防水微型摄影机后行走如常,为团队拍出大开眼界、如梦似幻的田中影片。(作品请见《福寿螺胡撇仔》(Golden Snail Opera))
.jpg)
其他在水田活跃的动物们也被相中,但是大番鸭激烈抗议把摄影机甩飞,狗儿花福则接下了这个任务,拍下在田埂上走跳时所见影像,也录下了它从泥土田埂跳到狭窄水泥田埂时跌倒所发出的惨叫声,证实了田埂的水泥化对生物造成的影响。
蔡晏霖还近距离拍摄了福寿螺卵粒一一孵化的瞬间,以及水稻开花的缩时摄影。她在论文中写道,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把“人”还原到“本有”的位置上,也就是一个物物相系、生死交织的网络中的环节之一。
在阿根廷,没人介意福寿螺,螺类学者喜相逢
台湾把福寿螺视为头号公敌,连不务农的人看见粉红色卵块都会心生嫌恶。那么在福寿螺的原乡──阿根廷,此螺与人类、与整个生态环境的关系又是什么?
“当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福寿螺有危害,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原生种,”常以福寿螺为创作灵感的Över说,当地农人看见田间有许多福寿螺造成的洞,还以为是打雷的关系,而民众更是没概念,以为螺卵是青蛙蛋呢!
原以为福寿螺在老家必定舒适过活,结果竟然“没有想像中的happy。”Över解释,那边的稻田是采取“干式直播”法,播种后等秧苗长大以后再放水,此时福寿螺已经啃不动。
.jpg)
还有天敌的威胁,“有两种以福寿螺为主食的鸟类,螺鹰和秧鹤,所以那边没有福寿螺还真的不行,不然这些物种会受到影响,”Över说。
最有趣的是阿根廷的学者们见到远来访客,相见恨晚热情以待,不仅纷纷拿出瓶瓶罐罐的螺类珍藏,更热心带着他们到处寻螺。台湾团也回报以别出心裁的福寿螺造型巧克力礼盒,以及螺卵贴纸等周边设计精品。
.jpg)
生物本无罪,要做友善农业,就要先认识它
“福寿螺反映了我们对农业的思考,比较主流的想法是,只要有生物进到田里,通通不要最好,也不想认识。”身为生物学者的林芳仪发现,过去台湾对福寿螺的研究,焦点都放在如何防治,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生物。
林芳仪和先生陈毅翰从生态角度切入,研究捕螺陷阱,探讨哪种诱饵最有效。过去农民就会在田中丢弃菜叶杂草诱捕福寿螺,他们实验则发现,米糠的效果最佳,每个陷阱“一个晚上可以捕捉一两百颗,就少弯腰两百次。”
她也好奇,其他国家到底如何对抗福寿螺?根据文献,1970年代福寿螺来到亚洲,第一站就是台湾,之后四散传播到日本、菲律宾、中国、韩国、泰国等地。
福寿螺考察团于是也去了日本和菲律宾,有了意外的发现。菲律宾有些农民是用一种植物碱让福寿螺的嘴巴肿起来无法进食,等消肿后,秧苗也长大了。而日本也有一些友善小农和福寿螺关系非常平和,林芳仪说,“我们去拜访的农民,都说福寿螺不是问题,他们田里也是有一定的量,甚至形容福寿螺是‘稻守贝’。”

在日本,从秧苗杀手变身稻米守护神
在台湾被骂成“夭寿螺”,在日本怎么会变成“稻守贝”?团队发现,日本只有本州中部以南较有福寿螺问题,且多数稻田是水旱轮作,不利福寿螺生存,不像宜兰二期休耕时田中还是放满了水。虽然惯行农民仍是用药防治,不过仍有友善小农尝试多元做法,透过对于当地气候的掌握和对于福寿螺生命史的了解,调整尝试出人螺的并存之道。
方法之一是是穴盘育苗,待秧苗成长四十天、长出四、五片叶子后才移到田间,福寿螺已经啃不动。二是干式直播,与阿根廷稻田做法雷同,在干地播下种子,待秧苗长壮才放水进来,此时福寿螺只能啃食刚冒出的杂草,反而变成农夫的好帮手,才得了“稻守贝”美称。
那么台湾是否可能透过改变耕作模式,降低福寿螺危害?林芳仪认为,要这么做必须要能控制水位、田地也要打得够平,而目前台湾稻作体系高度仰赖代耕,小农没有机械,育苗亦大都掌握在业者手中。不过宜兰小农可以先做实验,目前已经计划引进适合的小型日本插秧机。
在美洲,福寿螺喂饱众生,还拯救濒绝螺鹰
而在阿根廷,生物学家也看到了福寿螺在当地,扮演的是被掠食的底层角色。鳄鱼、蛇、浣熊、螺鹰、秧鹤,都把福寿螺当餐点,例如螺鹰喜欢站在木桩上大快朵颐,周围遍布螺壳,是为“螺冢”。而且由于福寿螺分布一直往北移动,原本在美国佛州快绝种的螺鹰,还因此而增加了数量,“所以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很难说!”
林芳仪总括,放置陷阱只是短期措施,中期计划是调整农耕模式,长期计划则是借由栖地营造,召唤福寿螺的天敌。“生物课本说,福寿螺在台湾没有天敌,这句要删掉。我们在田间观察,红冠水鸡、白腹秧鸡、彩鹬、柴棺龟都会吃它,”有研究曾经在柴棺龟大便里面发现七百多个福寿螺的壳口盖。
柴棺龟的别称叫做“米龟”,稻田里原本到处都是,如今却因栖地破坏而绝迹,上述的诸多鸟类也芳踪杳杳。于是插满了嫩嫩秧苗的稻田,就成为福寿螺的天堂,无穷无尽吃到饱的buffet。
.jpg) 折扣信息
网上购物大全
买得易网
双鱼座
水瓶座
摩羯座
射手座
天蝎座
天秤座
咖啡网
瑰夏咖啡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手磨咖啡
咖啡豆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云南咖啡
咖啡
耶加雪菲
咖啡网
瑰夏咖啡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手磨咖啡
咖啡豆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云南咖啡
咖啡
耶加雪菲
折扣信息
网上购物大全
买得易网
双鱼座
水瓶座
摩羯座
射手座
天蝎座
天秤座
咖啡网
瑰夏咖啡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手磨咖啡
咖啡豆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云南咖啡
咖啡
耶加雪菲
咖啡网
瑰夏咖啡
手冲咖啡和咖啡机区别
手磨咖啡
咖啡豆
精品咖啡豆
花魁咖啡
云南咖啡
咖啡
耶加雪菲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9-12-31 15:10:00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2.本站的原创文章,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不尊重原创的行为我们将追究责任;3.作者投稿可能会经我们编辑修改或补充。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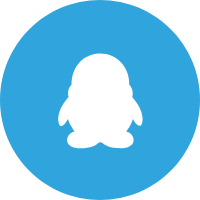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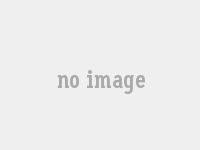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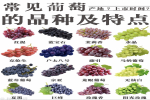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