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行政院宣布为地方创生元年,期望如同日本一样,透过基层公务员也能翻转地方,开启乡村地区的新契机,并且回应台湾的乡村问题、都市问题。但是不少人质疑,在一个以乡镇公所作为主要提案者的机制下,是否能够避免现有已知的民主制度相关弊病?基层公务人员又能否突破地方的派系、政治酬庸的常态,以及台湾地方乡镇公所的政治情境?若是在乡镇公所首长支持,地方创生政策又要怎么贴合地方需求,突破少数精英的困境?
今年度花莲县瑞穗乡公所的案例,将社区营造与审议民主共同结合,作为他们地方创生的前期准备工作,期望突破公所困境,建立跟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他们这一年的案例,值得我们省思。

“投打对决”中的地方创生
瑞穗乡公所民政课课长锺亚霖、民政课课员潘美琪,便是这一次案例的主角。他们明白,作为地方创生政策的元年,最首要的事情并不是立马规划提案,向中央提出地方创生政策。他们反而开始重新关注乡镇内的社区营造协会。潘美琪认为:“地方创生政策若意图解决地方问题,那么过去长达25年的社区总体营造,其所积累的社区能量与地方意识,会是地方创生的前哨战……”。
这一番话其来有自。社区营造在1993年提出的当下,便有意地绕过乡镇公所,其积极的意义,是期望社造政策能避免在草创的阶段,面临到乡镇公所这个以民意为依托的“庞然大物”,使得各个社区协会沦为乡镇公所操作下的傀儡;其消极的意义,则是乡镇公所作为一个地方自治机关,坦白地说──即是中央机关拿它没辙,因此干脆期望民间的能量能够弥补公务机关的延宕、程序等的问题,真正的贴合地方产生实践作为。
经过25年的社造历程,乡镇公所在社区总体营造中,成为了一个暧昧及尴尬的角色,许多时候一众社区看见便视若无睹、自动绕道。长久下来,社区总体营造的实践一旦面临到乡镇内的公家机关与政策时,难免产生制肘,或相关地方实践工作并未能整体推动等的问题。

在地方创生政策提出之前,文化部在社造政策中,便积极地透过“行政社造化”期望回首解决乡镇公所与社区之间的问题。但不论公务机构的社造培力与行政社造化的推展效益,在地方创生元年的当下,国发会悍然地以乡镇公所作为提案者,某种程度上强迫公所与社区之间必须互动。
有些论者认为,在地方创生中社区与公所会处于如同“投打对决”般的情境,轮番站上打席与投手丘;于是乡镇公所与社区在系列的攻防战中,看对方投出“长照”球、“闲置空间”球、“在地就业”球⋯⋯,另一方又要如何挥棒(偶尔也有“外援”入场);居民们便且看双方在这样的对决中,是否真的能够抛弃胜负,为彼此献上一场重唤球迷热情的比赛。

但是瑞穗乡公所,他们并未选择将彼此放在投手丘与打席上,他们寻找社区与公所在地方实践上的另一种可能。
以审议民主结合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
今年四月,花莲县文化局的社区营造三期征选报告中。锺亚霖课长偕同潘美琪二人在台上报告。他们坦言:虽然文化部近年来倡议审议民主,期望协助公所机关避免陷入民主制度中的“多数决”与“寡头政治”问题;但在地方创生元年的当下,他们更期望的事情是,借由审议民主的方式,迫使乡镇公所必须得听到社区的声音,同时也让社区抛弃原有的村落为疆界,以“乡”或扩大至文化生活范围,重新思考地方问题。
过去少有乡镇公所愿意以审议民主的方式倾听地方声音,因为一旦民众的声音透过文字、会议等记录下来时,他们便有必要解决民众所提出的问题。多数的公务人员与机关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但是瑞穗乡公所反其道而行,这令当时列席的委员与花莲文化局都感到惊讶。
询问着他们原因,潘美琪的回答值得令人省思:“如果地方创生政策面对的是地方不可回避的问题,要公务员们坐在办公室想着要提什么样的内容,一面担忧失败,一面又畏惧著民意代表或议员的质询;那么为何不让民众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做?……如果真的不幸地,最后的内容未达到我们所设想的。那也没关系,我们与民众一起承担、一起讨论,就算再失败,又能失败到哪里?”。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9-11-02 11:28:00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2.本站的原创文章,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不尊重原创的行为我们将追究责任;3.作者投稿可能会经我们编辑修改或补充。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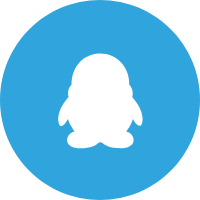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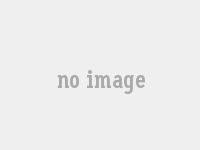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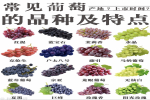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